专访NI亚太区商业航天负责人刘金龙:天上卫星到底多不多?
时间:2021-08-06 21:53:07来源:Lwgzc手游网作者:佚名我要评论 用手机看

扫描二维码随身看资讯
使用手机 二维码应用 扫描右侧二维码,您可以
1. 在手机上细细品读~
2. 分享给您的微信好友或朋友圈~
全球在轨卫星4000多颗,天上的卫星算不算多?为何要建低轨卫星互联网?未来的通信是否一定会用上卫星?建设卫星互联网,机遇和挑战在哪里?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cn)记者日前在上海专访了NI亚太区商业航天行业负责人刘金龙。刘金龙在航空航天与国防行业相关测试业务上有16年的经验。他曾深度参与国内第一家商业卫星公司创新测试体系的建立,见证了这些创新测试技术支撑国内第一颗商业卫星的成功发射并实现20颗卫星以上的星座组网过程。
目前来看,无论是遥感卫星还是通信卫星,数量“供给不足”。“发射数百颗低轨卫星就可能覆盖全球,但在任意一个点上,一旦打电话的人多了就服务不了了。为什么要发几万颗卫星也是这个道理。”
刘金龙表示,如果从通信的角度看,甚至和中国的地面基站数量相比,“几万颗卫星其实一点也不多”。
而目前,全世界的在轨服务的卫星只有4000多颗。4000多颗卫星绕着地球运转是否“拥挤”?刘金龙打了个形象的比方, “如果在地球上放4000多辆车,好像都不需要红绿灯了。”当然,卫星有轨道、有频率,从这个角度看是稀缺资源。
在大批量卫星上天前,是卫星网络的规划。刘金龙表示,首先要突破理论问题,包括发射多少颗卫星、采用什么频段通信、用什么编码方式。在天上还没有卫星时,地面实验室就需要模拟出星座原型的情况。
“很多人说为什么不见中国的卫星大批量上天?这些理论问题不解决,发了卫星以后也要迭代。卫星最大的问题是发上去就回不来了。”
卫星互联网建设的中下游环节是卫星制造和地面终端制造,而将商业器件用于商业航天的技术创新难度一点也不小。“把一个卫星终端做得非常小、成本非常低,也是非常难的。”就连SpaceX这样的企业,也在谋求降低终端成本,将几千美元的设备降低到几百美元。
卫星通信与5G通信融合的下一代天空地海一体化通信网络是NI较早提出的一个研究方向。未来的通信是否一定会用上卫星?刘金龙表示,目前来看,卫星的可能性更大。“对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希望的是没有感觉到有卫星的参加,但卫星真正在里面成为复杂的异构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做卫星的人往下看,做地面蜂窝网络的人往上看,但“相遇并不总是很甜蜜的一件事”。把5G原封不动搬上卫星是无法通信的,把卫星通信搬到地面的通信效率太低,卫星通信网络和地面通信网络在通信体制上的差距巨大,如何融合又是一个挑战。
如何看待中国卫星互联网建设存在的机遇和挑战,刘金龙说,要坚持第一性的物理原则,困难要一分为二地看,一部分是技术攻关性的困难,另一部分是随着发展就能慢慢解决的困难。
而人们总对机遇的认识不够完善,“航天人有个词叫星辰大海,现在被很多行业的人都借用了。你看不到星辰大海,也就看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
卫星互联网产业需要充分的基建时间,商业航天公司所做的每一步技术创新、商业创新都能产生价值,这是激励行业不断前进的很大动力。
中国商业航天从2014年兴起,在走过的这六七年时间里,已经有两枚民营火箭将卫星送入轨道,民营卫星工厂正拔地而起,多家商业航天公司获得10亿元以上融资,年发射规模100发的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也要来了。
2020年4月,卫星互联网纳入新基建,这给了中国商业航天一剂强心针,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一行业。而SpaceX也帮助全球了解这一市场,一家明星企业让全世界更多人认识到商业航天。
刘金龙认为,中国的商业航天正处于发展早期,但这几年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资本的介入代表未来或有较大商业价值,这是一个好表征。
“我们看到的是既整体处于初期又处于一个加速的翻天覆地变化的行业,也孕育很多新的机会。大家现在还抱成一团,在相对混沌、在各种技术创新中,很快就会有一些清晰的赛道出来。”
至于谁会在这个清晰的赛道里占据领先位置,成为头部企业,刘金龙认为,四个因素很重要:技术迭代形成的壁垒、给中青年技术设计师更多实践机会、不同产业的融合以及体制外的灵活优势。
作为跨国公司,NI创立至今已有40多年,开发了众多自动化测试和自动化测量系统,应用于各行各业。
以下是采访实录:
【卫星太多还是太少?为何要发展低轨卫星互联网?】
澎湃新闻:去年4月,卫星互联网纳入新基建。从你的角度谈谈卫星互联网作为新基建的提法给NI和上下游产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刘金龙: 卫星互联网目前是我们航天领域的第一大热门领域。我们在去年4月看到国家发改委把它纳入新基建时也非常振奋,但并不震惊。
实际上我们参与这件事情远远早于2020年4月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航天科工集团的鸿雁和虹云星座首发星都是在2018年底发射的。我们在那样的时间节点前就已经参与到卫星互联网相关的技术工作中了。
如果让我们谈卫星互联网,不管是基于通信服务还是遥感服务,过去从单颗卫星完成特定的国家任务,到能够逐渐进行商业化探索、走向星座,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大变化。
从技术角度来说也是非常振奋的。从单颗卫星到几百颗卫星带来的巨大挑战绝不只是从1到100这么简单,其实里面有更大的技术挑战。
澎湃新闻:现在有很多商业卫星公司都在造卫星工厂。在你看来,现在商业卫星发展到了什么阶段?需要这么多卫星、有这么大的需求吗?
刘金龙: 国内主流的创业公司跟我们都有很深入的交流,因为要有创新的产品首先得有创新的工具,而我们就是提供这种创新工具的企业。就在这个四楼的会议室,我曾经接待过这些创业公司的技术负责人。
谈到需求,我们就得溯源了。卫星也不是最终需求,发射卫星也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卫星提供服务。
从服务的角度说,卫星够不够?卫星所提供的服务现在是否已经达到了人们的预期?我是从业者,我也在思考。有人说卫星太多了,依据是什么?或者觉得卫星太少了,依据又是什么?
我们的依据是,卫星服务是否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比如遥感卫星服务目前市场规模并不是非常大,基本是政府在用。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政府用还不够呢。
比如你住一个很大的房子,你想监测房子周围的情况。这颗卫星告诉你,它一天能拍一张照片,而你的期望是20分钟拍一张,APP随时拿起来看院子的情况。
20分钟拍一张,价格可以非常高;一天只能拍一张,价值非常小。甚至我们现在也很难做到一天就给你家一个小区域拍一张照,所以卫星服务明显处于供给不足的情况。
通信卫星也是类似的情况。去年去青海湖自驾,我也是看到基站了赶紧把手机拿出来发个微信,大部分时候也是没有信号的。或者有信号,但都是基于语音服务的,可以理解为处于2G时代。而现在人们的需求很多不是语音通话,而是大带宽的数据,要上传视频、看视频。
澎湃新闻:所以你认为卫星是供给不足。
刘金龙: 对。为什么要发展低轨卫星互联网?因为高轨无法满足带宽和延时上的需求。低轨卫星基本上几小时就已经绕地球一圈了。打一颗这种卫星上去,真正能够在中国一个地点接受通信服务的时间太短了,这种通信服务几乎是没有商业价值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发射这么多卫星,卫星互联网规划里有几千颗几万颗卫星。
大家容易混淆覆盖和带宽的问题。发射数百颗卫星就可能覆盖全球了,但在任意一个点上,一旦打电话的人多了就服务不了了。为什么要发几万颗卫星也是这个道理。
并且一个工厂的建设,从有理念到能够稳定生产卫星,这是要遵循客观规律的。虽然中国是“基建狂魔”,但这不是盖住宅,不只是有厂房。
做卫星有很多环境设备,要模拟太空中温度的变化,太空中的热真空、电磁、振动,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时间调试,形成稳定产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我个人观点来看,目前没有看到过剩。当然做更合理的规划,这也是必要的。
【大批量卫星上天前先突破理论,商业器件技术创新难度一点不小】
澎湃新闻:NI的技术主要用在航天哪些领域?
刘金龙: 以构建卫星通信网络为例,首先要突破理论问题,发射多少颗卫星、采用什么通信体制、用什么编码方式,这些是前期研究,我们主要提供一些研究平台,在没有卫星时,在地面实验室模拟出星座原型的情况。
大家都说5G要上卫星了,我们要试一下,这个距离内加上这个信道,5G行不行?不行怎么改?这就要在前期研究阶段在平台上做,而不是发一颗卫星再来做一个实验,我们主要做这样的原型系统,可以说目前在国内是领先的。
再到中间阶段就是卫星制造,我们把很多商用的成熟技术拿到卫星领域使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
而NI的一些硬件产品都是在众多行业以几万的量级验证过的,把它拿过来用,起码可靠性毋庸置疑,在这个基础上再做技术创新,用另一种方式显著降低成本,也更数字化。
过去卫星行业就存在过度测试的问题。从元器件到单机再到整星,每个环节都要测试,因为数据是很难贯通的,数字化程度做得还不够。我们借鉴消费电子、汽车行业,把各个环节产生的数据收集起来,不需要耗费很多精力重复测试,以设备为基础推动数字化。
澎湃新闻:听起来像“数字孪生”,在卫星发上天之前把所有能够测试的全测试完,任何改动都能反馈到最终端,完备之后再上天组网。
刘金龙: 完全同意。你讲的“数字孪生”,或者我们叫“数字化”、“地面仿真验证网络”,这是同一个范畴,也是技术难度最大的。
很多人说为什么不见中国的卫星大批量上天?这些理论问题不解决,发了卫星以后也要迭代。卫星最大的问题是发上去就回不来了,所谓的迭代就是放弃了那颗再发一颗新的,但轨道和频率是宝贵的稀缺资源。
有一种观点认为太空的卫星不多,全世界在轨也才4000多颗。相比在地球上放4000多辆车,好像不需要红绿灯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它又是有轨道有频率的,没有频率就像没有线的风筝。
所以理论这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是值得的,目前国内很多同行在这个领域里突破,一旦我们能跟地面网络做很好的融合,我们就可以利用地面通信网络的产业链。
澎湃新闻:刚刚提到数字化上需要有突破,商业航天领域还有哪些技术需要去突破的?
刘金龙: 技术突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从0到1,这基本可以不计成本和时间。这样的突破在航天领域更多是空间站、深空探测。
还有一种技术突破也非常难。在可负担的成本下、有商业价值的情况下,这种技术创新的难度也不小。我们要把一个卫星终端做得非常小、成本非常低,也是非常难的。
因为这意味着要采取和过去传统航天不一样的技术路线。一旦采用不一样的技术路线,那就是从一个很薄弱的技术开始做起。无论是卫星制造还是地面制造都面临同样的问题。SpaceX也宣称在卫星上用了大量商业元器件。既然用了这么多商业级器件,带来的挑战就很大了。
SpaceX的“星舰”已经做到十几个原型了,它的材料是从未用过的。一旦成功,收益是大的。这是高精尖吗?
所以这个技术创新的难度是在另一个赛道上,和我们做深空探测、载人航天是不一样的赛道,在可负担成本的情况下,结合一些地面的成熟应用,这个挑战其实一点也不小。
【做卫星的人往下看,做地面蜂窝网络的人往上看】
澎湃新闻:卫星通信与5G通信融合的下一代天空地海一体化通信网络是什么?
刘金龙: 这实际上是我们目前技术投入最大的一块,也是我们认为技术难度最大的。
从4G到5G的跨越,只是地面蜂窝网络的跨越,全世界投入了多少研发成本?现在要把蜂窝网络从地面扩展到天空地海一体化的网络。
如果想象我们站在火星看地球,地球人的通信还是基于地球表面,坐热气球上天还不能打电话、看视频,这就是天空地海一体化信息网络的使命。
过去像美国的facebook、google曾尝试用低空气球构建空间网络,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它都需要很大的能源,因为低空气球要浮在那里。
这就是为什么把卫星互联网和地面蜂窝网络拉在一起了,因为要覆盖更广的地域范围以及空间,包括海上,海上的通信问题还没有解决。
为什么融合很重要?因为融合一张网络以后客户的体验会更好,否则就变成了在这里用一个手机,到了海上得换一个终端,我要连上卫星的网络。
或者我去旅游要带两个终端,一个连基站,另一个连卫星网络。显然人们的需求是能否有一张融合的网络,能够让人们在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访问,也就是所谓的全球数字化,消除数字鸿沟。
澎湃新闻:目前的研究进展如何,有哪些挑战,未来会有怎样的应用场景?
刘金龙: 卫星的通信网络和地面的通信网络过去通信体制上的差距是巨大的,怎么去融合?
两波人在推动,一波做卫星通信的人要兼容地面的蜂窝网络,另一波人说5G现在已经开始商用了,总要往前进发满足人们未来的需求。做地面蜂窝网络的这些科研工作者做什么呢?我不敢说未来6G是确定的方向,但至少大家都不约而同认为把卫星加进来是一个比较确定的方向。
做卫星的人往下看,做地面蜂窝网络的人往上看,大家相遇了。相遇并不总是很甜蜜的一件事,因为难度非常大,这两者的通信信道特点不同,卫星高速移动,你什么时候看见基站在转悠?
卫星大概以几公里每秒的速度移动,你在路上开一个超跑,你俩的相对速度再加上地球的转动,这就有多大的相对速度了?搞通信的人最怕就是两者都动,信道实时变化。
从业内角度来说,就是怎么设计下一代通信网络体制的问题,这就是巨大挑战。把5G搬到卫星上,显然原封不动是没法通信的。把卫星通信搬到地面,通信效率太低了,频谱的利用率也太低了,这就存在融合的挑战。
要做成这样一件事,国内产业界的同仁都往前走,光喊口号还不行,咱们还得拿实物去做,NI就做这件事,我们过去既做过卫星的通信网络,又做过地面的5G网络。
理论问题先解决,要不然我应该造一个什么样的卫星?应该放什么样的通信器件?遵循什么样的通信体制呢?
澎湃新闻:未来的通信一定会用上卫星?
刘金龙: 对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希望的是没有感觉到有卫星的参加,但卫星真正在里面成为复杂的异构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是不是一定是卫星?目前来看,卫星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相比于其他各种手段,目前卫星从技术、商业的角度来说,是比较可行的方式。
【卫星互联网产业需要充分的基建时间,先满足一部分市场需求】
澎湃新闻:你认为现在的商业航天公司距离形成商业闭环是否还有一段距离?
刘金龙: 其实这也是业界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我认为必须得加一个词:机遇。
既然没有完整的商业闭环,大家在里面都会有自己的细分机会。你做的每一步技术创新、商业上的创新都能产生价值,这是激励整个行业不断前进的很大动力,它不是一成不变、一潭死水的行业。
卫星产业链分为上游的卫星制造和发射,中端是卫星运营,下端是卫星应用。卫星制造占全球的商业价值只有10%不到。卫星制造跟卫星运营相比所产生的产值是低的,卫星的发射也不多,更多的都是运营及应用。
说到商业闭环,一个新型基础设施在建立之初还没有产生很大商业价值时,自然不能完善整个商业闭环,但雏形已经开始出现了。
比如卫星物联网、卫星对于船舶的AIS识别(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应急通信,比如中国的天通卫星目前对中国的国土以及沿海的覆盖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只不过很多时候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
基本上我看到的很多商业卫星公司都以全产业链为目标导向,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产业发展初期的必经阶段,要不了多久一定会出现分化。卫星制造、运营、地面应用是差异化比较大的市场。
未来会不会有公司全覆盖?我相信会有,但会有很多专业化的公司在专业的赛道里,只做卫星制造、只做卫星运营、只做卫星地面应用。
所以说到不闭环,我倒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负面的事情,因为目前来看,中国打上去的真正低轨通信的卫星不超过10颗。网络的雏形都还没有,我们商业没闭环这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物联网卫星我们发射得多一些,在一些局部领域已经开始落地闭环了,只不过这远离to C场景。
我相信,卫星互联网产业也需要有充分的基建时间,况且这个基建的速度也不会快,因为卫星的发射还受制于诸多因素,比如发射场的资源、发射工位、火箭,总之需要一个过程。
但我想不是等所有卫星互联网基本上构建完成了商业才开始,而是先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比如物联网的需求、偏远地区的通信需求,再到满足更多人的高精度定位需求,逐渐走向更大的市场。
商业闭环不是一个0和1的状态,在我看来是一个过程,技术不断进步,满足更多需求,体验更好。
【车企布局卫星互联网,垂直领域的竞争者加速商业落地】
澎湃新闻:商业航天里也有汽车企业在布局卫星互联网。怎样看待来自于垂直领域的参赛者加入到这个赛道中,包括未来在应用上挖掘增量市场?
刘金龙: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带来的垂直赛道可以大大加速商业闭环的周期。它和其他商业公司的区别在于,它已经谋定了一个不一定是唯一的目标市场,但至少它已经有一个依托。
SpaceX前段时间发布了车载卫星终端,车和卫星之间产生某种联系。垂直赛道带来确定性,但是否拘泥于这个市场,我觉得肯定会有横向的扩张。因为本质上来说,它的卫星和其他没有谋定一个细分市场的卫星公司也没有太大差异,也不是说它不能去做其他的市场,只不过加速了商业闭环的周期,它会比别人节省一部分时间,因为还有很多商业公司一边发卫星一边还在想市场在哪、瞄准什么,是做农业,还是林业,还是应急救灾,或者是物联网?
垂直商业公司进来,对推动商业闭环、商业落地是一个加速器。它代表了从用户端、落地端的资本力量进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澎湃新闻:卫星互联网企业面临着一个怎样的应用端现状?未来会不会像你提到的,从用户的角度倒逼上游发展,开拓未来的应用市场?未来的应用在哪里?
刘金龙: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建完了去产生应用,另一种是用户有需要,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在没有4G的时代,老百姓也没有想过随时随地要上传一个视频。你问一个开汽车的人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汽车能在天上飞,我想也许会有,但能不能形成一种很强有力的消费呼声去呼吁这样的设施出来,我表示有很大的疑虑。
过去从北京飞到上海两个小时,我觉得不上网挺好的,能休息。但自从有了比较慢速的WiFi,我发现我离不开它了,那两个小时和客户微信沟通也很有价值。
从这里看到,飞机上用到卫星互联网是很有必要的,有可能我在飞机上就可以开视频会议了,目前还不行,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飞机用的还是高轨的(卫星),延时比较大,视频多媒体信息还是比较难发送,基本上以文字为主。
澎湃新闻:所以主要是前期基础设施建设完再引发一种需求?
刘金龙: 是的,并且在没建之前也要触发。我们在卫星领域怀有商业梦想的这群人,他们触发了想象。想象得多了,形成了一种消费呼声的时候,这些设施就会有了,就像有魔法一样。
当年4G的建设者也没有想到像抖音这样的应用吧。可能他想到了一部分需求,触发了老百姓的商业需求,到后边枝叶蔓延,这是我们这些做基础设施的人无法想象的。
推演的路线图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触发一部分比较刚性的痛点,比如应急通信、偏远地区的5G回传。再进一步还能干什么?能不能从纽约到上海一个小时内到达?各行各业基于自己的需求,呼吁航天从业者给它提供更便利的东西。我们先触发一下,他们再把需求提得更多,我们的基础设施越建越好,这个行业就繁荣起来了,也带来了更多商业价值。
【商业航天这几年翻天覆地,给中青年技术设计师更多实践机会】
澎湃新闻:去年多家商业航天公司获得10亿元以上融资,第二枚民营火箭入轨,很多公司也在造卫星工厂。从2014年商业航天兴起发展到现在的六七年时间里,行业的变化过程是怎样的?
刘金龙: 首先我们的判断是,这个行业处于发展早期。但我也可以用另一个词来形容这几年的变化:翻天覆地。过去航天产业是没有资本介入的,资本介入代表了它未来可能有比较大的商业价值,这是一个很好的表征。
但如果类比其他行业,这个融资是太多了吗?是太少了。对比卫星的造价,几十到百公斤级的卫星,那也是千万级别的费用,并且一颗星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说这些融资能造几颗卫星?我想未来会有更多的资本,包括产业资本会进入这个行业。
我们看到的是既整体处于初期又处于一个加速的翻天覆地变化的行业,也孕育很多新的机会。大家现在还抱成一团,在相对混沌、在各种技术创新中,很快就会有一些清晰的赛道出来。
这时候可能还看不出来谁会在这个清晰的赛道里占据领先位置,这取决于这个阶段的积累。
澎湃新闻:你认为哪些因素可能促成出现一些头部企业?
刘金龙: 我们有一些观察,在技术上投入比较大、走得比较前的公司、研究机构,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分化。就跟PPT造车一样,PPT造星。说实话,卫星这个产业,PPT造星真的是迫不得已。
我先为我们业界的朋友说几句,毕竟通过这我们才吸引到了这么点投资,也没有产生泡沫。你看花了钱的公司都发了卫星。还没发的,那就是PPT造星还没拿到支持,这个行业目前还没有泡沫。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长光卫星在短短的时间内,同样功能、性能的卫星,重量和成本都是以十倍级的速度减少的,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二个赛道上的创新,也是极其关键的,这才支撑了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头部企业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些基础设施不是短期能够形成的,它的生产规模、效率,卫星的迭代次数,都给后来者奠定了很高的时间成本,即使得到资本的支持,也需要时间去做这样的技术迭代。
这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卫星很大的壁垒就在于迭代。卫星一旦上去一颗,要迭代就得下一颗了。这时候长光卫星的团队是怎么锻炼出来的?我曾经也就这个问题深刻地访问过他们。
我们最后达成的共识就是给年轻人机会,给年轻人一个迭代的平台,让他参与一颗星的研制,他觉得有精进的空间,下一颗星他还做主设计师,再下一颗还去造,这种体验是跨越式的,这是过去这个行业内最缺乏的。
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体制内的一些领导也在媒体上发声,如果我们商业航天的发展没有带来增量,只是从体制内转移了一部分技术力量,这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我们看到,真正要想走向头部的商业卫星公司,一定不是完全基于这条道路的,它一定是带来了不同产业的融合、体制外的灵活优势,给了中青年技术设计师更多实践机会,带动了技术进步和人才的培养。
【看不到星辰大海,也就看不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澎湃新闻:最后做个总结,要建设卫星互联网,会面临哪些机遇,又会面临哪些痛点、难点?
刘金龙: 我们的大脑很有意思,可以简单分成两块,一块产生了大胆有创意的想法,但很快又被另外一半大脑中住的管家给管住了,这个不行,这个实现不了,这个有困难。
这里头应该怎么看待这种机遇和挑战,我觉得应该坚持第一性的物理原则,是有物理上不能突破的点吗?还是可克服的困难?我们看到卫星互联网的重大机遇,但那些困难是不是我们一步一步走就可以克服的?如果回顾过去的路,实际上都是慢慢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是不是先把机遇的部分看得更完整,把未来的推演做得更完善?
所以这些困难,我倒觉得要一分为二地看。一部分是技术攻关性的困难,是世界上还没有的东西。一部分是随着发展能慢慢解决的。
人们谈困难谈得比较多,我们被另一个管家给管住了,总是想了很多困难,机遇的部分认识得不够完善。你还没有看到那么巨大的潜力,如果看清楚,会产生很多细分的赛道,产业资本也好,创业者也好,都会进入的。
澎湃新闻:SpaceX对国内商业航天的发展带来哪些思考?
刘金龙: 某种意义上来说,SpaceX帮助全球了解这个市场,有这样一家明星企业让全世界更多的人知道商业航天。
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真的认为它是基于雄厚的产业链来做的。这不是完全的个人英雄主义,一家把所有事都做了。
第三个层面,它能大胆利用技术创新是值得钦佩的,比如在控制阶段大量采用过去所不采用的技术。创新技术的运用对于国内同行,给了我们更多勇气去探索,也营造了一个良好环境。
至于技术上有多少借鉴,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走不同的路。它的技术是否在未来一定是最领先的?不一定。
处于这种技术路线探索的过程中,尤其像中国,地面蜂窝网络的通信技术过去几年快速进步,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国内人才基础。(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cn)记者日前在上海专访了NI亚太区商业航天行业负责人刘金龙。刘金龙在航空航天与国防行业相关测试业务上有16年的经验。他曾深度参与国内第一家商业卫星公司创新测试体系的建立,见证了这些创新测试技术支撑国内第一颗商业卫星的成功发射并实现20颗卫星以上的星座组网过程。

刘金龙
刘金龙在回答前述问题时表示,卫星并非最终需求,发射卫星也不是最终目的。天上的卫星多不多,评判依据是卫星服务是否满足了人们的需求。目前来看,无论是遥感卫星还是通信卫星,数量“供给不足”。“发射数百颗低轨卫星就可能覆盖全球,但在任意一个点上,一旦打电话的人多了就服务不了了。为什么要发几万颗卫星也是这个道理。”
刘金龙表示,如果从通信的角度看,甚至和中国的地面基站数量相比,“几万颗卫星其实一点也不多”。
而目前,全世界的在轨服务的卫星只有4000多颗。4000多颗卫星绕着地球运转是否“拥挤”?刘金龙打了个形象的比方, “如果在地球上放4000多辆车,好像都不需要红绿灯了。”当然,卫星有轨道、有频率,从这个角度看是稀缺资源。
在大批量卫星上天前,是卫星网络的规划。刘金龙表示,首先要突破理论问题,包括发射多少颗卫星、采用什么频段通信、用什么编码方式。在天上还没有卫星时,地面实验室就需要模拟出星座原型的情况。
“很多人说为什么不见中国的卫星大批量上天?这些理论问题不解决,发了卫星以后也要迭代。卫星最大的问题是发上去就回不来了。”
卫星互联网建设的中下游环节是卫星制造和地面终端制造,而将商业器件用于商业航天的技术创新难度一点也不小。“把一个卫星终端做得非常小、成本非常低,也是非常难的。”就连SpaceX这样的企业,也在谋求降低终端成本,将几千美元的设备降低到几百美元。
卫星通信与5G通信融合的下一代天空地海一体化通信网络是NI较早提出的一个研究方向。未来的通信是否一定会用上卫星?刘金龙表示,目前来看,卫星的可能性更大。“对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希望的是没有感觉到有卫星的参加,但卫星真正在里面成为复杂的异构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做卫星的人往下看,做地面蜂窝网络的人往上看,但“相遇并不总是很甜蜜的一件事”。把5G原封不动搬上卫星是无法通信的,把卫星通信搬到地面的通信效率太低,卫星通信网络和地面通信网络在通信体制上的差距巨大,如何融合又是一个挑战。
如何看待中国卫星互联网建设存在的机遇和挑战,刘金龙说,要坚持第一性的物理原则,困难要一分为二地看,一部分是技术攻关性的困难,另一部分是随着发展就能慢慢解决的困难。
而人们总对机遇的认识不够完善,“航天人有个词叫星辰大海,现在被很多行业的人都借用了。你看不到星辰大海,也就看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
卫星互联网产业需要充分的基建时间,商业航天公司所做的每一步技术创新、商业创新都能产生价值,这是激励行业不断前进的很大动力。
中国商业航天从2014年兴起,在走过的这六七年时间里,已经有两枚民营火箭将卫星送入轨道,民营卫星工厂正拔地而起,多家商业航天公司获得10亿元以上融资,年发射规模100发的国际商业航天发射中心也要来了。
2020年4月,卫星互联网纳入新基建,这给了中国商业航天一剂强心针,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一行业。而SpaceX也帮助全球了解这一市场,一家明星企业让全世界更多人认识到商业航天。
刘金龙认为,中国的商业航天正处于发展早期,但这几年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资本的介入代表未来或有较大商业价值,这是一个好表征。
“我们看到的是既整体处于初期又处于一个加速的翻天覆地变化的行业,也孕育很多新的机会。大家现在还抱成一团,在相对混沌、在各种技术创新中,很快就会有一些清晰的赛道出来。”
至于谁会在这个清晰的赛道里占据领先位置,成为头部企业,刘金龙认为,四个因素很重要:技术迭代形成的壁垒、给中青年技术设计师更多实践机会、不同产业的融合以及体制外的灵活优势。
作为跨国公司,NI创立至今已有40多年,开发了众多自动化测试和自动化测量系统,应用于各行各业。
以下是采访实录:
【卫星太多还是太少?为何要发展低轨卫星互联网?】
澎湃新闻:去年4月,卫星互联网纳入新基建。从你的角度谈谈卫星互联网作为新基建的提法给NI和上下游产业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刘金龙: 卫星互联网目前是我们航天领域的第一大热门领域。我们在去年4月看到国家发改委把它纳入新基建时也非常振奋,但并不震惊。
实际上我们参与这件事情远远早于2020年4月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和航天科工集团的鸿雁和虹云星座首发星都是在2018年底发射的。我们在那样的时间节点前就已经参与到卫星互联网相关的技术工作中了。
如果让我们谈卫星互联网,不管是基于通信服务还是遥感服务,过去从单颗卫星完成特定的国家任务,到能够逐渐进行商业化探索、走向星座,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大变化。
从技术角度来说也是非常振奋的。从单颗卫星到几百颗卫星带来的巨大挑战绝不只是从1到100这么简单,其实里面有更大的技术挑战。
澎湃新闻:现在有很多商业卫星公司都在造卫星工厂。在你看来,现在商业卫星发展到了什么阶段?需要这么多卫星、有这么大的需求吗?
刘金龙: 国内主流的创业公司跟我们都有很深入的交流,因为要有创新的产品首先得有创新的工具,而我们就是提供这种创新工具的企业。就在这个四楼的会议室,我曾经接待过这些创业公司的技术负责人。
谈到需求,我们就得溯源了。卫星也不是最终需求,发射卫星也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卫星提供服务。
从服务的角度说,卫星够不够?卫星所提供的服务现在是否已经达到了人们的预期?我是从业者,我也在思考。有人说卫星太多了,依据是什么?或者觉得卫星太少了,依据又是什么?
我们的依据是,卫星服务是否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比如遥感卫星服务目前市场规模并不是非常大,基本是政府在用。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政府用还不够呢。

吉林一号拍摄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图片来自“吉林一号”微信公众号
中国的遥感卫星数量不是太多。如果跟做遥感的卫星公司谈,问他们的产品为什么现在还处于市场前期开发阶段。在他们看来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卫星数量不够。比如你住一个很大的房子,你想监测房子周围的情况。这颗卫星告诉你,它一天能拍一张照片,而你的期望是20分钟拍一张,APP随时拿起来看院子的情况。
20分钟拍一张,价格可以非常高;一天只能拍一张,价值非常小。甚至我们现在也很难做到一天就给你家一个小区域拍一张照,所以卫星服务明显处于供给不足的情况。
通信卫星也是类似的情况。去年去青海湖自驾,我也是看到基站了赶紧把手机拿出来发个微信,大部分时候也是没有信号的。或者有信号,但都是基于语音服务的,可以理解为处于2G时代。而现在人们的需求很多不是语音通话,而是大带宽的数据,要上传视频、看视频。
澎湃新闻:所以你认为卫星是供给不足。
刘金龙: 对。为什么要发展低轨卫星互联网?因为高轨无法满足带宽和延时上的需求。低轨卫星基本上几小时就已经绕地球一圈了。打一颗这种卫星上去,真正能够在中国一个地点接受通信服务的时间太短了,这种通信服务几乎是没有商业价值的。这就是为什么要发射这么多卫星,卫星互联网规划里有几千颗几万颗卫星。
大家容易混淆覆盖和带宽的问题。发射数百颗卫星就可能覆盖全球了,但在任意一个点上,一旦打电话的人多了就服务不了了。为什么要发几万颗卫星也是这个道理。

图片来自网络
和基站比比,几万颗卫星其实一点也不多。别说全球了,中国有多少基站?我相信这是以十万百万来计的。在我们看来,卫星不是过多,而是供给不足。并且一个工厂的建设,从有理念到能够稳定生产卫星,这是要遵循客观规律的。虽然中国是“基建狂魔”,但这不是盖住宅,不只是有厂房。
做卫星有很多环境设备,要模拟太空中温度的变化,太空中的热真空、电磁、振动,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时间调试,形成稳定产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我个人观点来看,目前没有看到过剩。当然做更合理的规划,这也是必要的。
【大批量卫星上天前先突破理论,商业器件技术创新难度一点不小】
澎湃新闻:NI的技术主要用在航天哪些领域?
刘金龙: 以构建卫星通信网络为例,首先要突破理论问题,发射多少颗卫星、采用什么通信体制、用什么编码方式,这些是前期研究,我们主要提供一些研究平台,在没有卫星时,在地面实验室模拟出星座原型的情况。
大家都说5G要上卫星了,我们要试一下,这个距离内加上这个信道,5G行不行?不行怎么改?这就要在前期研究阶段在平台上做,而不是发一颗卫星再来做一个实验,我们主要做这样的原型系统,可以说目前在国内是领先的。
再到中间阶段就是卫星制造,我们把很多商用的成熟技术拿到卫星领域使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

卫星民企银河航天南通卫星超级工厂
以地面设备为例,因为这个市场的规模不够有吸引力,过去都是一些小型公司在做,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强度不够。同样的,因为一年只有这么些卫星,地面设备数量也不会多于这个,没有充分的时间去迭代,导致无论是可靠性还是创新的程度都会有很大挑战。而NI的一些硬件产品都是在众多行业以几万的量级验证过的,把它拿过来用,起码可靠性毋庸置疑,在这个基础上再做技术创新,用另一种方式显著降低成本,也更数字化。
过去卫星行业就存在过度测试的问题。从元器件到单机再到整星,每个环节都要测试,因为数据是很难贯通的,数字化程度做得还不够。我们借鉴消费电子、汽车行业,把各个环节产生的数据收集起来,不需要耗费很多精力重复测试,以设备为基础推动数字化。
澎湃新闻:听起来像“数字孪生”,在卫星发上天之前把所有能够测试的全测试完,任何改动都能反馈到最终端,完备之后再上天组网。
刘金龙: 完全同意。你讲的“数字孪生”,或者我们叫“数字化”、“地面仿真验证网络”,这是同一个范畴,也是技术难度最大的。
很多人说为什么不见中国的卫星大批量上天?这些理论问题不解决,发了卫星以后也要迭代。卫星最大的问题是发上去就回不来了,所谓的迭代就是放弃了那颗再发一颗新的,但轨道和频率是宝贵的稀缺资源。
有一种观点认为太空的卫星不多,全世界在轨也才4000多颗。相比在地球上放4000多辆车,好像不需要红绿灯了。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它又是有轨道有频率的,没有频率就像没有线的风筝。
所以理论这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是值得的,目前国内很多同行在这个领域里突破,一旦我们能跟地面网络做很好的融合,我们就可以利用地面通信网络的产业链。
澎湃新闻:刚刚提到数字化上需要有突破,商业航天领域还有哪些技术需要去突破的?
刘金龙: 技术突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从0到1,这基本可以不计成本和时间。这样的突破在航天领域更多是空间站、深空探测。
还有一种技术突破也非常难。在可负担的成本下、有商业价值的情况下,这种技术创新的难度也不小。我们要把一个卫星终端做得非常小、成本非常低,也是非常难的。
因为这意味着要采取和过去传统航天不一样的技术路线。一旦采用不一样的技术路线,那就是从一个很薄弱的技术开始做起。无论是卫星制造还是地面制造都面临同样的问题。SpaceX也宣称在卫星上用了大量商业元器件。既然用了这么多商业级器件,带来的挑战就很大了。
SpaceX的“星舰”已经做到十几个原型了,它的材料是从未用过的。一旦成功,收益是大的。这是高精尖吗?
所以这个技术创新的难度是在另一个赛道上,和我们做深空探测、载人航天是不一样的赛道,在可负担成本的情况下,结合一些地面的成熟应用,这个挑战其实一点也不小。
【做卫星的人往下看,做地面蜂窝网络的人往上看】
澎湃新闻:卫星通信与5G通信融合的下一代天空地海一体化通信网络是什么?
刘金龙: 这实际上是我们目前技术投入最大的一块,也是我们认为技术难度最大的。
从4G到5G的跨越,只是地面蜂窝网络的跨越,全世界投入了多少研发成本?现在要把蜂窝网络从地面扩展到天空地海一体化的网络。
如果想象我们站在火星看地球,地球人的通信还是基于地球表面,坐热气球上天还不能打电话、看视频,这就是天空地海一体化信息网络的使命。
过去像美国的facebook、google曾尝试用低空气球构建空间网络,过去没有解决的问题是它都需要很大的能源,因为低空气球要浮在那里。

SpaceX星链卫星
只有卫星,并且是低轨的卫星,我们一般认为在500公里到2000公里的范围内。这就是为什么把卫星互联网和地面蜂窝网络拉在一起了,因为要覆盖更广的地域范围以及空间,包括海上,海上的通信问题还没有解决。
为什么融合很重要?因为融合一张网络以后客户的体验会更好,否则就变成了在这里用一个手机,到了海上得换一个终端,我要连上卫星的网络。
或者我去旅游要带两个终端,一个连基站,另一个连卫星网络。显然人们的需求是能否有一张融合的网络,能够让人们在任何空间和任何时间访问,也就是所谓的全球数字化,消除数字鸿沟。
澎湃新闻:目前的研究进展如何,有哪些挑战,未来会有怎样的应用场景?
刘金龙: 卫星的通信网络和地面的通信网络过去通信体制上的差距是巨大的,怎么去融合?
两波人在推动,一波做卫星通信的人要兼容地面的蜂窝网络,另一波人说5G现在已经开始商用了,总要往前进发满足人们未来的需求。做地面蜂窝网络的这些科研工作者做什么呢?我不敢说未来6G是确定的方向,但至少大家都不约而同认为把卫星加进来是一个比较确定的方向。
做卫星的人往下看,做地面蜂窝网络的人往上看,大家相遇了。相遇并不总是很甜蜜的一件事,因为难度非常大,这两者的通信信道特点不同,卫星高速移动,你什么时候看见基站在转悠?
卫星大概以几公里每秒的速度移动,你在路上开一个超跑,你俩的相对速度再加上地球的转动,这就有多大的相对速度了?搞通信的人最怕就是两者都动,信道实时变化。
从业内角度来说,就是怎么设计下一代通信网络体制的问题,这就是巨大挑战。把5G搬到卫星上,显然原封不动是没法通信的。把卫星通信搬到地面,通信效率太低了,频谱的利用率也太低了,这就存在融合的挑战。
要做成这样一件事,国内产业界的同仁都往前走,光喊口号还不行,咱们还得拿实物去做,NI就做这件事,我们过去既做过卫星的通信网络,又做过地面的5G网络。
理论问题先解决,要不然我应该造一个什么样的卫星?应该放什么样的通信器件?遵循什么样的通信体制呢?
澎湃新闻:未来的通信一定会用上卫星?
刘金龙: 对普通用户来说,我们希望的是没有感觉到有卫星的参加,但卫星真正在里面成为复杂的异构网络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是不是一定是卫星?目前来看,卫星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相比于其他各种手段,目前卫星从技术、商业的角度来说,是比较可行的方式。
【卫星互联网产业需要充分的基建时间,先满足一部分市场需求】
澎湃新闻:你认为现在的商业航天公司距离形成商业闭环是否还有一段距离?
刘金龙: 其实这也是业界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我认为必须得加一个词:机遇。
既然没有完整的商业闭环,大家在里面都会有自己的细分机会。你做的每一步技术创新、商业上的创新都能产生价值,这是激励整个行业不断前进的很大动力,它不是一成不变、一潭死水的行业。
卫星产业链分为上游的卫星制造和发射,中端是卫星运营,下端是卫星应用。卫星制造占全球的商业价值只有10%不到。卫星制造跟卫星运营相比所产生的产值是低的,卫星的发射也不多,更多的都是运营及应用。
说到商业闭环,一个新型基础设施在建立之初还没有产生很大商业价值时,自然不能完善整个商业闭环,但雏形已经开始出现了。
比如卫星物联网、卫星对于船舶的AIS识别(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应急通信,比如中国的天通卫星目前对中国的国土以及沿海的覆盖已经做得非常好了,只不过很多时候离我们的生活太远了。
基本上我看到的很多商业卫星公司都以全产业链为目标导向,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产业发展初期的必经阶段,要不了多久一定会出现分化。卫星制造、运营、地面应用是差异化比较大的市场。
未来会不会有公司全覆盖?我相信会有,但会有很多专业化的公司在专业的赛道里,只做卫星制造、只做卫星运营、只做卫星地面应用。
所以说到不闭环,我倒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负面的事情,因为目前来看,中国打上去的真正低轨通信的卫星不超过10颗。网络的雏形都还没有,我们商业没闭环这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物联网卫星我们发射得多一些,在一些局部领域已经开始落地闭环了,只不过这远离to C场景。
我相信,卫星互联网产业也需要有充分的基建时间,况且这个基建的速度也不会快,因为卫星的发射还受制于诸多因素,比如发射场的资源、发射工位、火箭,总之需要一个过程。
但我想不是等所有卫星互联网基本上构建完成了商业才开始,而是先满足一部分人的需求,比如物联网的需求、偏远地区的通信需求,再到满足更多人的高精度定位需求,逐渐走向更大的市场。
商业闭环不是一个0和1的状态,在我看来是一个过程,技术不断进步,满足更多需求,体验更好。
【车企布局卫星互联网,垂直领域的竞争者加速商业落地】
澎湃新闻:商业航天里也有汽车企业在布局卫星互联网。怎样看待来自于垂直领域的参赛者加入到这个赛道中,包括未来在应用上挖掘增量市场?
刘金龙: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带来的垂直赛道可以大大加速商业闭环的周期。它和其他商业公司的区别在于,它已经谋定了一个不一定是唯一的目标市场,但至少它已经有一个依托。
SpaceX前段时间发布了车载卫星终端,车和卫星之间产生某种联系。垂直赛道带来确定性,但是否拘泥于这个市场,我觉得肯定会有横向的扩张。因为本质上来说,它的卫星和其他没有谋定一个细分市场的卫星公司也没有太大差异,也不是说它不能去做其他的市场,只不过加速了商业闭环的周期,它会比别人节省一部分时间,因为还有很多商业公司一边发卫星一边还在想市场在哪、瞄准什么,是做农业,还是林业,还是应急救灾,或者是物联网?
垂直商业公司进来,对推动商业闭环、商业落地是一个加速器。它代表了从用户端、落地端的资本力量进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澎湃新闻:卫星互联网企业面临着一个怎样的应用端现状?未来会不会像你提到的,从用户的角度倒逼上游发展,开拓未来的应用市场?未来的应用在哪里?
刘金龙: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基础设施的建设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建完了去产生应用,另一种是用户有需要,前者的可能性更大。
在没有4G的时代,老百姓也没有想过随时随地要上传一个视频。你问一个开汽车的人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汽车能在天上飞,我想也许会有,但能不能形成一种很强有力的消费呼声去呼吁这样的设施出来,我表示有很大的疑虑。
过去从北京飞到上海两个小时,我觉得不上网挺好的,能休息。但自从有了比较慢速的WiFi,我发现我离不开它了,那两个小时和客户微信沟通也很有价值。
从这里看到,飞机上用到卫星互联网是很有必要的,有可能我在飞机上就可以开视频会议了,目前还不行,因为现在我们中国的飞机用的还是高轨的(卫星),延时比较大,视频多媒体信息还是比较难发送,基本上以文字为主。
澎湃新闻:所以主要是前期基础设施建设完再引发一种需求?
刘金龙: 是的,并且在没建之前也要触发。我们在卫星领域怀有商业梦想的这群人,他们触发了想象。想象得多了,形成了一种消费呼声的时候,这些设施就会有了,就像有魔法一样。
当年4G的建设者也没有想到像抖音这样的应用吧。可能他想到了一部分需求,触发了老百姓的商业需求,到后边枝叶蔓延,这是我们这些做基础设施的人无法想象的。
推演的路线图应该是这样的,我们触发一部分比较刚性的痛点,比如应急通信、偏远地区的5G回传。再进一步还能干什么?能不能从纽约到上海一个小时内到达?各行各业基于自己的需求,呼吁航天从业者给它提供更便利的东西。我们先触发一下,他们再把需求提得更多,我们的基础设施越建越好,这个行业就繁荣起来了,也带来了更多商业价值。
【商业航天这几年翻天覆地,给中青年技术设计师更多实践机会】
澎湃新闻:去年多家商业航天公司获得10亿元以上融资,第二枚民营火箭入轨,很多公司也在造卫星工厂。从2014年商业航天兴起发展到现在的六七年时间里,行业的变化过程是怎样的?
刘金龙: 首先我们的判断是,这个行业处于发展早期。但我也可以用另一个词来形容这几年的变化:翻天覆地。过去航天产业是没有资本介入的,资本介入代表了它未来可能有比较大的商业价值,这是一个很好的表征。
但如果类比其他行业,这个融资是太多了吗?是太少了。对比卫星的造价,几十到百公斤级的卫星,那也是千万级别的费用,并且一颗星还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你说这些融资能造几颗卫星?我想未来会有更多的资本,包括产业资本会进入这个行业。

卫星民企九天微星唐山卫星工厂
过去航天领域投资不活跃主要是它的商业落地不成熟,目前来看不但探索出了一个方向,同时大大加快了落地速度。建设速度快,能够更快产生商业价值,这会促进更多资本进入,又会形成正向循环,推动这个行业更快速往前走。我们看到的是既整体处于初期又处于一个加速的翻天覆地变化的行业,也孕育很多新的机会。大家现在还抱成一团,在相对混沌、在各种技术创新中,很快就会有一些清晰的赛道出来。
这时候可能还看不出来谁会在这个清晰的赛道里占据领先位置,这取决于这个阶段的积累。
澎湃新闻:你认为哪些因素可能促成出现一些头部企业?
刘金龙: 我们有一些观察,在技术上投入比较大、走得比较前的公司、研究机构,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分化。就跟PPT造车一样,PPT造星。说实话,卫星这个产业,PPT造星真的是迫不得已。
我先为我们业界的朋友说几句,毕竟通过这我们才吸引到了这么点投资,也没有产生泡沫。你看花了钱的公司都发了卫星。还没发的,那就是PPT造星还没拿到支持,这个行业目前还没有泡沫。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长光卫星在短短的时间内,同样功能、性能的卫星,重量和成本都是以十倍级的速度减少的,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二个赛道上的创新,也是极其关键的,这才支撑了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头部企业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些基础设施不是短期能够形成的,它的生产规模、效率,卫星的迭代次数,都给后来者奠定了很高的时间成本,即使得到资本的支持,也需要时间去做这样的技术迭代。
这也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卫星很大的壁垒就在于迭代。卫星一旦上去一颗,要迭代就得下一颗了。这时候长光卫星的团队是怎么锻炼出来的?我曾经也就这个问题深刻地访问过他们。
我们最后达成的共识就是给年轻人机会,给年轻人一个迭代的平台,让他参与一颗星的研制,他觉得有精进的空间,下一颗星他还做主设计师,再下一颗还去造,这种体验是跨越式的,这是过去这个行业内最缺乏的。
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体制内的一些领导也在媒体上发声,如果我们商业航天的发展没有带来增量,只是从体制内转移了一部分技术力量,这对整个产业的发展是没有好处的。
我们看到,真正要想走向头部的商业卫星公司,一定不是完全基于这条道路的,它一定是带来了不同产业的融合、体制外的灵活优势,给了中青年技术设计师更多实践机会,带动了技术进步和人才的培养。
【看不到星辰大海,也就看不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澎湃新闻:最后做个总结,要建设卫星互联网,会面临哪些机遇,又会面临哪些痛点、难点?
刘金龙: 我们的大脑很有意思,可以简单分成两块,一块产生了大胆有创意的想法,但很快又被另外一半大脑中住的管家给管住了,这个不行,这个实现不了,这个有困难。
这里头应该怎么看待这种机遇和挑战,我觉得应该坚持第一性的物理原则,是有物理上不能突破的点吗?还是可克服的困难?我们看到卫星互联网的重大机遇,但那些困难是不是我们一步一步走就可以克服的?如果回顾过去的路,实际上都是慢慢可以克服这些困难的。是不是先把机遇的部分看得更完整,把未来的推演做得更完善?
所以这些困难,我倒觉得要一分为二地看。一部分是技术攻关性的困难,是世界上还没有的东西。一部分是随着发展能慢慢解决的。

中国首枚发射入轨的民营火箭双曲线一号遥一 。陈肖 摄
比如商业火箭为什么发射成本很高?因为产量太低了。SpaceX现在是什么逻辑?它很快就会占据世界上西方国家发射很大的份额,它一旦没有外边的发射任务,就发射自己的星链卫星,它这么一直发射上去的最大好处是,它的技术炉火纯青,你跟它的成本没法比了。人们谈困难谈得比较多,我们被另一个管家给管住了,总是想了很多困难,机遇的部分认识得不够完善。你还没有看到那么巨大的潜力,如果看清楚,会产生很多细分的赛道,产业资本也好,创业者也好,都会进入的。

第二枚成功将卫星送入轨道的民营火箭谷神星一号遥一。陈肖 摄
所以机遇和挑战,我倒觉得过于强调现实困难,会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航天人有个词叫星辰大海,现在被很多行业的人都借用了。你看不到星辰大海,也就看不到解决这些问题的路径。澎湃新闻:SpaceX对国内商业航天的发展带来哪些思考?
刘金龙: 某种意义上来说,SpaceX帮助全球了解这个市场,有这样一家明星企业让全世界更多的人知道商业航天。
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真的认为它是基于雄厚的产业链来做的。这不是完全的个人英雄主义,一家把所有事都做了。
第三个层面,它能大胆利用技术创新是值得钦佩的,比如在控制阶段大量采用过去所不采用的技术。创新技术的运用对于国内同行,给了我们更多勇气去探索,也营造了一个良好环境。
至于技术上有多少借鉴,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是走不同的路。它的技术是否在未来一定是最领先的?不一定。
处于这种技术路线探索的过程中,尤其像中国,地面蜂窝网络的通信技术过去几年快速进步,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国内人才基础。(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热门手游下载
 天天绕圈圈游戏 1.2.5 安卓版
天天绕圈圈游戏 1.2.5 安卓版 加查海关与咖啡游戏 1.1.0 安卓版
加查海关与咖啡游戏 1.1.0 安卓版 大吉普越野驾驶游戏 1.0.4 安卓版
大吉普越野驾驶游戏 1.0.4 安卓版 沙盒星球建造游戏 1.5.0 安卓版
沙盒星球建造游戏 1.5.0 安卓版 秘堡埃德兰Elderand游戏 1.3.8 安卓版
秘堡埃德兰Elderand游戏 1.3.8 安卓版 地铁跑酷暗红双旦版 3.5.0 安卓版
地铁跑酷暗红双旦版 3.5.0 安卓版 跨越奔跑大师游戏 0.1 安卓版
跨越奔跑大师游戏 0.1 安卓版 Robot Warfare手机版 0.4.1 安卓版
Robot Warfare手机版 0.4.1 安卓版 地铁跑酷playmods版 3.18.2 安卓版
地铁跑酷playmods版 3.18.2 安卓版 我想成为影之强者游戏 1.11.1 官方版
我想成为影之强者游戏 1.11.1 官方版 gachalife2最新版 0.92 安卓版
gachalife2最新版 0.92 安卓版 航梦游戏编辑器最新版 1.0.6.8 安卓版
航梦游戏编辑器最新版 1.0.6.8 安卓版 喵星人入侵者游戏 1.0 安卓版
喵星人入侵者游戏 1.0 安卓版 地铁跑酷黑白水下城魔改版本 3.9.0 安卓版
地铁跑酷黑白水下城魔改版本 3.9.0 安卓版
相关文章
热门文章
- 1 小米手环充电没反应怎么办 小米手环无法充电解决方法
- 2 20余科学家发文称新冠病毒不可能是人为制造,专访第一作者
- 3 深圳灵明光子发布自主研发3D传感芯片,初步具备量产能力
- 4 万乘基因发布高通量单细胞测序仪,打破海外垄断国内市场现状
- 5 中国科学家提出一种新型固态原子钟方案,更适于实际应用
- 6 中国首个原创抗体偶联药物“出海”:交易额创纪录26亿美元
- 7 小米手环2闹钟怎么关闭 闹钟每隔10分钟就响一次解决方法
- 8 为何飞了这么久才到?落火之后做什么?设计师揭秘天问一号
- 9 这家上海机器人公司凭啥拿下丰田大单?背后有40年研发基因
- 10 科技部等多部门:支持女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更大作用
热门手游推荐
换一批
- 1
芭比公主宠物城堡游戏 1.9 安卓版
- 2
死神之影2游戏 0.42.0 安卓版
- 3
地铁跑酷忘忧10.0原神启动 安卓版
- 4
跨越奔跑大师游戏 0.1 安卓版
- 5
挂机小铁匠游戏 122 安卓版
- 6
咸鱼大翻身游戏 1.18397 安卓版
- 7
灵魂潮汐手游 0.45.3 安卓版
- 8
烤鱼大师小游戏 1.0.0 手机版
- 9
旋转陀螺多人对战游戏 1.3.1 安卓版
- 10
Escapist游戏 1.1 安卓版
- 1
开心消消乐赚钱版下载
- 2
Minecraft我的世界基岩版正版免费下载
- 3
暴力沙盒仇恨最新版2023
- 4
疯狂扯丝袜
- 5
黑暗密语2内置作弊菜单 1.0.0 安卓版
- 6
爆笑虫子大冒险内购版
- 7
姚记捕鱼
- 8
秘密邻居中文版
- 9
班班幼儿园手机版
- 10
千炮狂鲨





















 芭比公主宠物城堡游戏 1.9 安卓版
芭比公主宠物城堡游戏 1.9 安卓版 死神之影2游戏 0.42.0 安卓版
死神之影2游戏 0.42.0 安卓版 地铁跑酷忘忧10.0原神启动 安卓版
地铁跑酷忘忧10.0原神启动 安卓版 挂机小铁匠游戏 122 安卓版
挂机小铁匠游戏 122 安卓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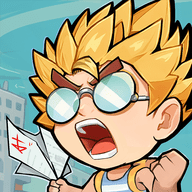 咸鱼大翻身游戏 1.18397 安卓版
咸鱼大翻身游戏 1.18397 安卓版 灵魂潮汐手游 0.45.3 安卓版
灵魂潮汐手游 0.45.3 安卓版 烤鱼大师小游戏 1.0.0 手机版
烤鱼大师小游戏 1.0.0 手机版 旋转陀螺多人对战游戏 1.3.1 安卓版
旋转陀螺多人对战游戏 1.3.1 安卓版 Escapist游戏 1.1 安卓版
Escapist游戏 1.1 安卓版 开心消消乐赚钱版下载
开心消消乐赚钱版下载 Minecraft我的世界基岩版正版免费下载
Minecraft我的世界基岩版正版免费下载 暴力沙盒仇恨最新版2023
暴力沙盒仇恨最新版2023 疯狂扯丝袜
疯狂扯丝袜 黑暗密语2内置作弊菜单 1.0.0 安卓版
黑暗密语2内置作弊菜单 1.0.0 安卓版 爆笑虫子大冒险内购版
爆笑虫子大冒险内购版 姚记捕鱼
姚记捕鱼 秘密邻居中文版
秘密邻居中文版 班班幼儿园手机版
班班幼儿园手机版 千炮狂鲨
千炮狂鲨